销开的沉古桐色遮了半个天地,我仰头望不见顶,四周弥漫着晨时的茫雾,遮了南荒野,掩了残冬林,晕开一片浸了酒的梅色,飞鸟的羽翅分割破晓,隐于天际的冷云,淡去了轮廓与影,不问归期。
山川空寂,风萧萧过千里,我路过此地,不见行客二一,庆幸。
杂草蛮横疯长过膝,铺了底,霜露沾了裤角,抖落一片碎冬,潮湿,泥泞,埋了深骨,视野所及之处一片枯秋昏黄,瑟瑟断弦筝筝响。
道路崎岖错落不平,乱石稀叠,各态形异,时而陡险,时而矩平,恍惚间误入旧柏竹林,几处暗,几处明,渐渐失了规,疑是陷局无路,徘徊之际,竟得一处泠泉凉溪。
汩汩流如岁冬月,岸边缀青,不得光处背石上垫了苔,四下清幽俱静,偶尔风过竹林,千万的叶奏出半弦的鸣,余音惊不起涟漪,似阖眼未睁的老者经了风霜,阅历无数,若是开口,便是七分世事,三分人间。
近午,古桐披了蓑衣,积淀了暗棕的调,山头染开混了泉的墨,如脂蒙了明。雾散,显了大半的层林,其间无序的抹了白,我知道,那是久经不化的眠冬雪,积成不可缺之的韵。
天地间除渐远时近的瀑流声,风过草瑟层林响,偶尔乍起鸟鸣,化于半空,抹开淡淡回音,于这山川,于这荒野与林,便是一份古老的穆静。
若是有俗人喧扰,怕是会惊动神灵。
我近了山的背面,去寻那一处离世的泉瀑,洗尽人间的繁芜杂琐,以喧嚣遮耳,以茫雾盖目,遮过皮,盖过骨,于心底自清自明。
无数大珠小珠散在脚边,构成白幕连天,耳畔充斥喧哗,视野模糊一片,微凉混着湿漉的空气钻进肺,四下弥漫开水汽,仿佛置身于雾里。
流瀑落下在岸石上激起的涧泉茫雾,朦胧了半面山,似与人间相分裂隔绝,再无关系,那一道白幕割离出骨,每个细碎的零珠都浸着久经岁年的古老历史,超度了棋局方寸,远高于人间。
被立于这喧哗磅礴之下,似被一名老者沉默不语,却又渡山重过水复的注视,淡去,视野所及的高度晕开了茫,压了乌云的灰,零珠碎玉飞溅于石,漫开冰冷的冬意,如笙残缺。
我久久置身于这半山的幕,未言半分,四下散开无数的灵透彻了骨,与之共鸣,侧过身,水汽遮了视野湿了眼睫,于这喧哗磅礴之下于这老者注视之间,我阖了眸,垂首,虔诚,双手合十。
万物皆为灵。
山川空寂,不同于人间,而这半面背山瀑流看似方寸,实则破了局,露骨显灵。这老者应曾见过行及此的过客,却未困二一。
我久久立于此地而未睁眼,喧哗斥耳,骨浸满灵,心底虔诚不减半分,不语,双手合十,似乎也成了这无数灵中的万分之一,相互回应,与之共鸣。
我不过无数行客之一,只是于这老者的注视下,悟出了真谛。
行山客,人间喧扰,做自己的神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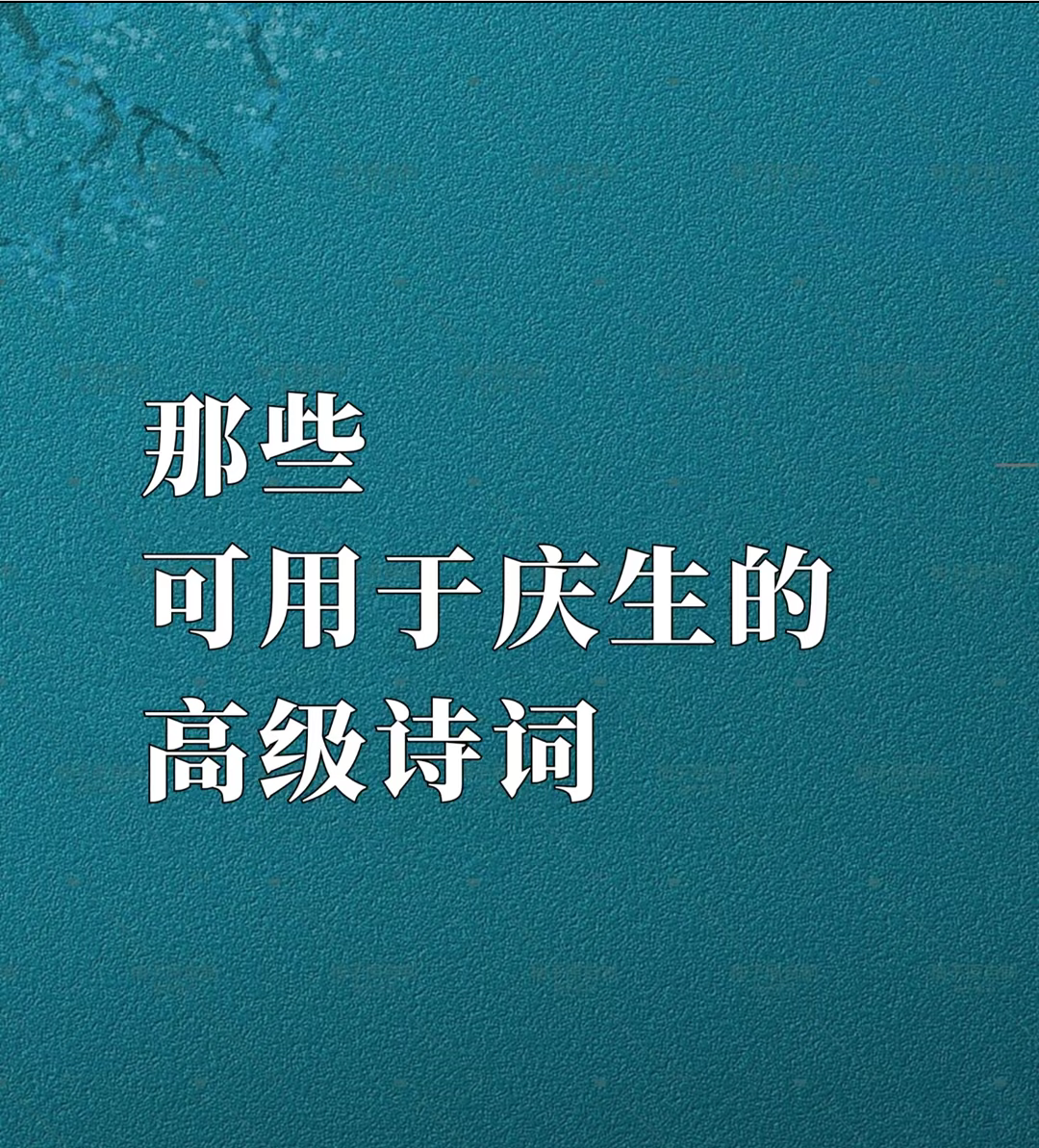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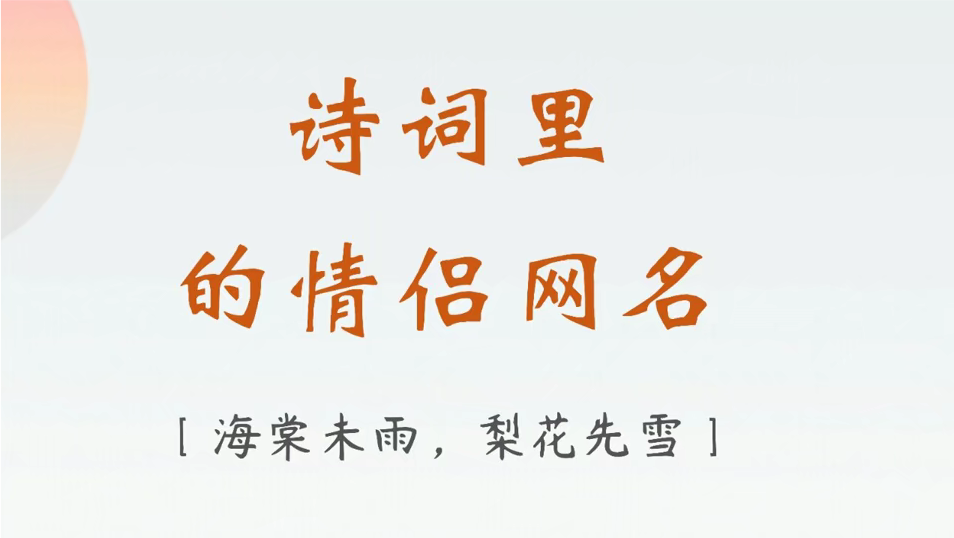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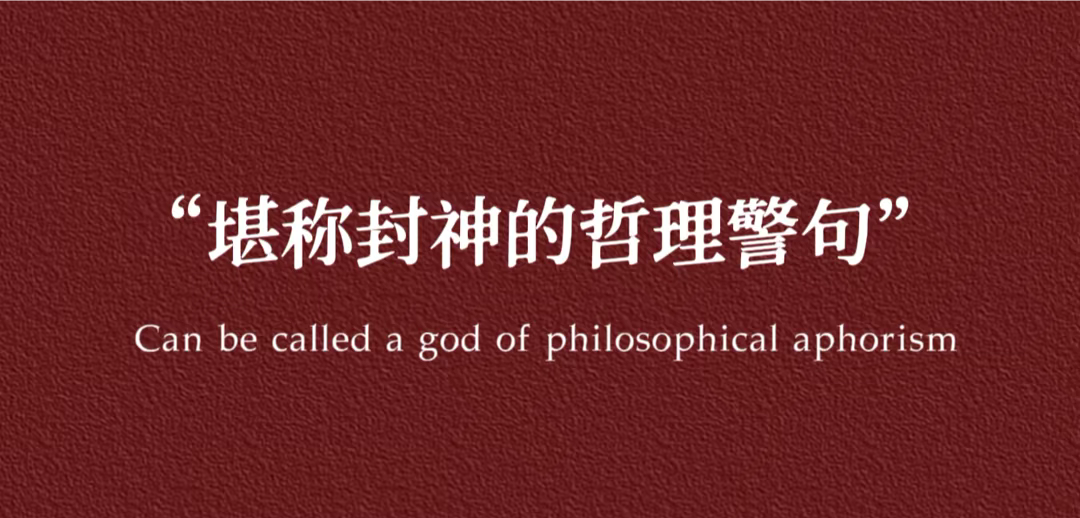




请登录后查看评论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