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南哲北上
他走在,一坪新刷的柏油路上,落日的阳光是填满天空的,道上只有夕阳还有披在他身上的红毯子,这毯子温哒哒的,在纤夫两肩透过,盖住小小的盒子。那是朝西的路堤下面是粼粼的水沟。稻谷与芦苇齐平,微微的随风。
那车夫的铃铛又变成了细萧,我第一次看见坝上有了绿牌子,嘀嗒—雁飞雁去.,萧萧秋风,散去多少人间筳席。唉,家里的锁又没划,锁心早就成淬烂的浮萍,一碰送同木框照片一起碎裂。唉!又忘了老房的样子,再也生硬的桎梏也破碎!哦《青年报》上曾刊登,亚洲第一天矿!唉!这记的,记的,就像你奶奶手,皱坑是岁月最重的刻物,他还是慢腾腾走在路上,夕阳当空垂下金色的挽联.,盖住了八月的北方稀土,土坝是高的,在这怅惘的天廖,那金色的大手又盖住了树.芦苇,伸张到没有尽头的秋,还有温暖,被红布盖着的,长方形盒子里的我。我飞在天空中,天上只有几滴云
而悲切的霞,那是天空的舟,这天河下、车夫后,巨大的矿坑延绵千里,群山尽拱,一派黑乌,我终于走出这矿坑了,我们一生热血奋献的地方。
我的连华,大口喝着一碗糁汤。盘膝坐在土炕上,这汤不知怎的,越渴越咸,咸的发苦.,要起身倒掉,火炝里的火苗人高亢,黑夜拉下帐联,寒风呼嗷吹过空树,白发,老树枝拍打窗框。铁锅里还有些余热,又拿上半瓶粮酒,轻轻拉掉暗红的铁丝,倒进卫兵时代的遗物,抿了几口,便一头昏胀在炕上,一副空虚的骨架,门口怎得有人高叩?有点醉的发蒙了。
连英屹在台前.,像塔上的雷锋塑像正正方方,下面道“雷锋第二故乡”“雷锋好榜样”连英竞觉得自己有些像,都是第二故乡,都是坚决自己所谓的“信念 ”连英笑了笑。新拉的节能灯飘乎不定,周围寂静,他又敲了了门,这时手里又凭空多了用铁盒载老花生米,一碗溜醋的焖肉段;油已经凝干,像干沉的旧毛巾,这时那尊朝着东方的塑像,我悄摸的爬在头上,看着连英,他总是跺脚踩着那,秋风飞去,再也飞不出凎润的黑。夜鸟惨睹着朦胧的矿山,月光飞不出深诲的坑。此刻飞灰漫卷,灰色涌动的深海下,有一个蹈矩的月亮,灰色的天空.。
门内有着一个没落的父亲,煤渣在他的胸膛挣扎,沿着气管,在爬不出去的喉口里看到光亮,又是嘶声的干咳。一块极小的煤渣咳出,却被焦急的儿子踩碎,他的灰有些被永远压在青石板上,有些则被儿子的鞋垫印刻,一片黑白的滩涂。
连英听到没有声音,连忙推门跑了进去,连华没事,转而质问为什么没有参加葬礼,又慢慢低头,看着饭菜,他吃过了。又默默地看着连英,连英拿着煤精模雕,迅速放进了那看不懂的东西,可连华知道这个机器是扫描仪,那是当年,光绪皇帝开辟西露天矿时,北迁的连华的太爷爷安家落户,用半生精力雕来的煤雕模子,那是祖宗传下来的,在日本人的刺刀下,太爷爷的朋友,徒弟,同乡全部血淋淋的倒在地上,横七竖八,太爷爷血泪交纵,死也紧紧抱着它,后来东北解放,这雕塑又回到了爷爷手里。他叫魁星踢斗。
这雕像里现在还有当年太爷爷的血泊,泪痕,浇筑了魂魄,之前他还是在祠堂里上过香火的。那双眼静谧,望着闪耀的,不灭的北斗七星。
现在,没有倭寇,没有俄人。自家的男丁却要忤逆,这充满灵性的器物,还是跳不过时代变迁的劫难吗?十年前,那是连英第一次来到义乌,他被南方的繁华震撼了,那是北方城市绝无仅有的生机,他深深盼切但他没想要驻足,而是忠贞自己的家乡。浑河水没有长江风清扬云,沙鸥翔集,但他是故乡的温柔,故土深沉的母爱。离了山海关,可最后一眼是玄菟古关门金黄的残阳,上面静止千年不断的星轮,高尔山脊垣断熟悉的古城,哪里还有努尔哈赤射在牌匾上的箭吏呢?时空过于苍白.。他决心振兴故土,当电商的时代于浩浩丁火卷起热潮时,他坚信这座失落的城市会被点燃。但没有原模的三维数据,只有粗糙的劣品,连英放下最后的尊言。他坚信,时代会把他们一家,这个城市,给予生命。
天空东边一道弦,矿坑上的嘹望塔还在闪烁,矿坑的东岗是大青树,当年主席曾一手扶持,眺望天矿。忽有一大鹏青鸟落于树上,朝东方欢叫三声飞去。现在,大青树上,我的坟前,日初朝升,一条光明铺满,琉璃腾涌的线。我的坟前,背后是朝阳,朝着大青树,树下是矿,我们一生热血奋献的地方。我看着左面两条溪水围拱的道路,我又听到了细萧,铃声。生生不息的芦苇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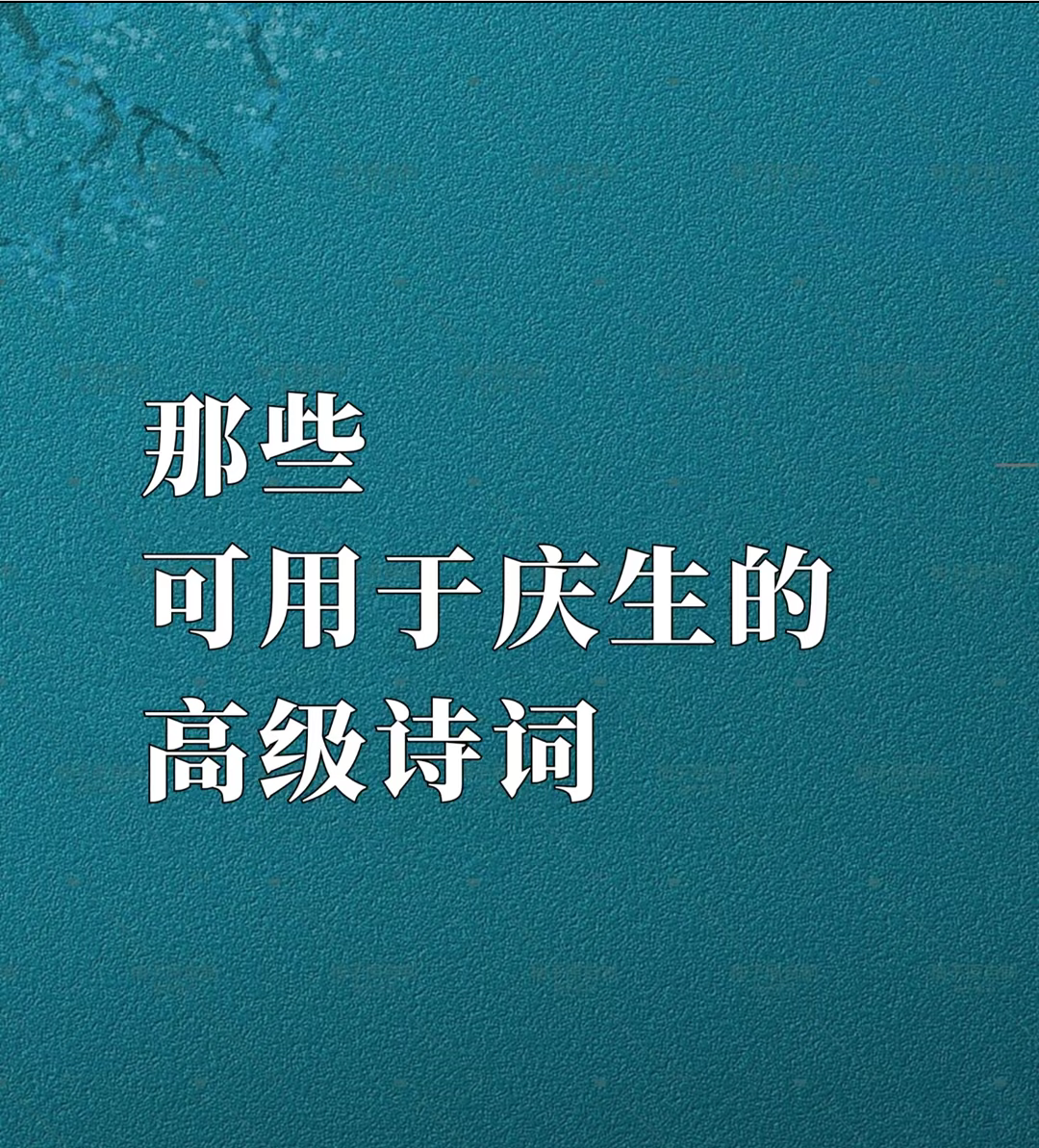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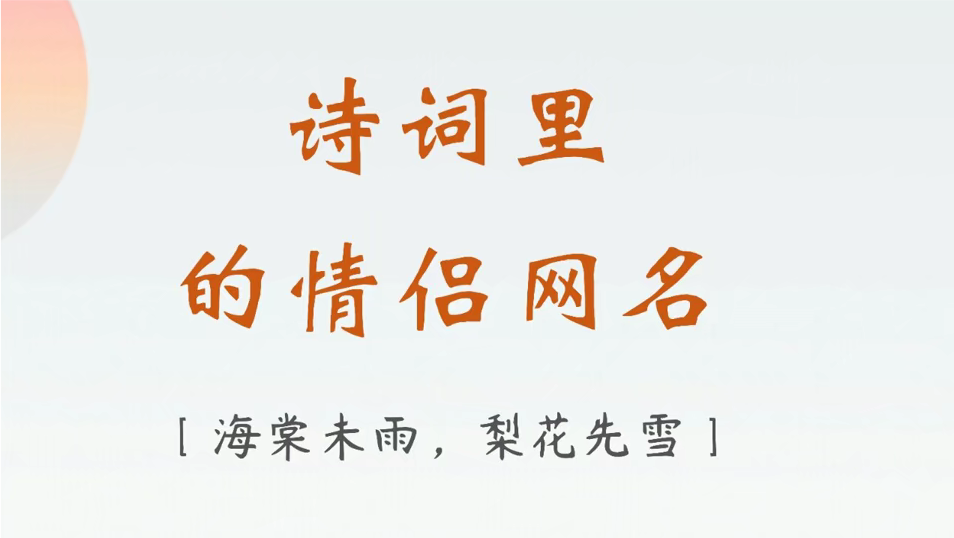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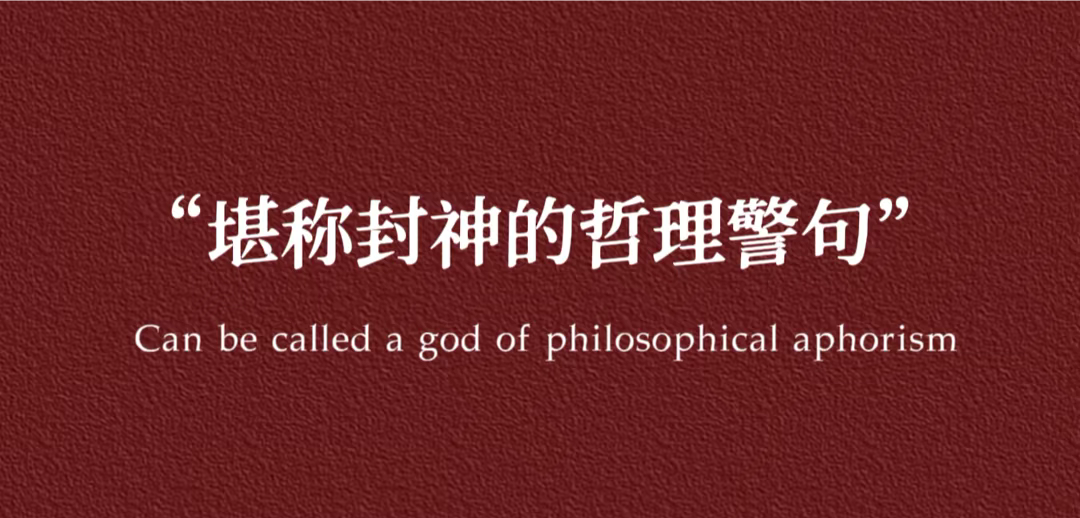




请登录后查看评论内容